广州康鹭制衣村:在“转型”浪潮中沉浮的小老板们|深度报道
时间:2023-04-27人气:作者:佚名

采写/李迎 赵萱
编辑/计巍

康乐村早上的招工街
夜晚的海珠区,广州塔灯火辉煌。相比城市夜间中的五光十色,四五公里外,康鹭城中村的繁华是由白炽灯组成的:一间间小制衣厂正赶制着凌晨即将运出的服装,它们将被连夜送至广州十三行、沙河等服装档口。
这是广州最著名的制衣村,一平方公里的片区内聚集了超十万人口,其中有八成以上来自湖北。“小单快返”的加工方式让这里一度成为广州制衣业的神话,有小制衣厂老板曾年入百万,不到五年便在广州买了房。对于这些湖北同乡而言,这里是理想的“淘金地”:从制衣工起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制衣厂老板,“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
“康鹭速度”曾在去年10月按下暂停键,海珠作为广州疫情最严重的区域,感染者大多分布在人口、房屋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12月1日,康鹭片区解封,但城中村治理问题在疫情期被进一步放大。
2023年2月,一纸拆违通知将许多小制衣厂老板从“淘金梦”中拉回现实。在拆违过程中,有人一夜之间从老板重新做回零工,焦虑和不安在小老板们之间传递,“现在只拆顶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都拆了”。对于康鹭片区城中村的改造,近些年他们听到的传闻不断,而这次拆违,或许是这些在广州服装纺织行业浪潮中沉浮的人,经历的第一次“退潮”。
他们不愿被留在岸上,但他们知道,这场“退潮”才刚刚开始。

康鹭片区被拆除的楼顶铁皮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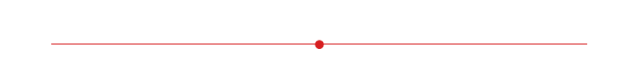
拆除“铁皮房”
“自3月1日起,康鹭片区集体物业所有顶楼非混凝土结构的临建不再出租并立即拆除,请租户做好随时搬迁的准备。”今年2月12日,接到拆违通知那天,制衣厂老板王芳正和厂里的工人们一起给雪纺衬衣钉上扣子。
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是广州最大的制衣村。康鹭临近中大布匹市场,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像王芳开办的这种小型制衣厂、印花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有5200余家。它们和工人宿舍一起,分布在狭窄街道两侧简陋的“握手楼”里。
那时正值年后复工,是康鹭片区制衣厂最忙的时候,王芳的厂子新接了一批夏装订单。怕影响厂里的工人,王芳赶紧从社区的人手里把通知接过来,收进抽屉。
这间150平米的厂房,是王芳和丈夫在2016年末买下的。制衣厂老板口中的“买厂”,实际是承租厂房并支付转让费,“给上一个老板几十万,接手他的厂和机器,之后每个月还要给房东付房租”,王芳说。
这个厂房在鹭江49号四楼,是一个三层楼顶上加盖的铁皮房。
“铁皮房”曾是康鹭片区制衣业日益红火的“标志”。
1993年,第一批服装加工厂入驻鹭江村,租下本地居民民宅作厂房,此后制衣厂在鹭江、康乐遍地开花。随着制衣厂的增多,当地村民开始加建楼层以获取更多租金。
加建的楼层多采用铁皮为顶,相较于原有楼层,顶层的“铁皮房”格局开阔,能摆下更多机器,房租和转让费也更便宜。为节约成本,越来越多的老板们租下这样的铁皮房开厂。
在这次的治理计划中,“铁皮房”是首要整改对象。“如果都拆的话,至少要拆这里五分之一的厂,这里几乎每一栋的楼顶都是后加盖的,都有厂。”王芳说。

未拆除前的康鹭片区顶楼铁皮房内的小制衣厂
为了不耽误加工进度,王芳立刻开始找新的厂房。在康乐村一家专门张贴卖厂信息的打印店里,她看上一个康乐一社的厂房,距离她现在的厂不远,搬起来不算困难。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建在楼顶,看起来很“安全”。几乎没再对比其他卖厂信息,王芳就匆忙定下这间厂房。
康鹭片区的制衣业以“小单快返”的模式闻名。每天下午3点前后,来自各服装批发市场的客户在中大布匹市场选面料、打版,然后将布料送至片区内的制衣厂加工。
裁剪缝合、熨烫锁边、剪线打包,次日凌晨,打包好的成衣从小制衣厂运出,发往广州十三行、白马、万佳等服装批发档口。康鹭制衣以“速度快”著称,客户们从购买原料到拿到成衣,一般不会超过两天。
去年10月,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曾让这样的“康鹭速度”按下暂停键。那时海珠区疫情严重,新增感染者大多数分布在人口、房屋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工人和老板们陆续被隔离、转运,整个片区被封控39天,生产交易陷入停滞。
12月1日,康鹭片区解封。王芳本以为恢复生产就在眼前,却从老乡口里听到“铁皮房”要被拆除的消息。
自去年12月起,海珠区开始逐步对城中村的违法建设进行治理。今年1月28日,海珠凤阳街道办事处发布的《致康乐鹭江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康乐鹭江片区正按照“拆、治、兴”要求稳步推进综合提升工作,其中包括片区人居环境治理提升、片区整体规划建设,以及片区产业形态引导等方面。
今年2月以来,康鹭片区几乎所有顶层制衣厂的老板都收到了搬迁通知。3月1日,刘利的丈夫接到社区发来的短信,要求其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届时将给予每平方米500元的补偿。
刘利的制衣厂位于康乐一社的一栋四层小楼的顶层,不到200平米的厂房里共20来台制衣机器。三月,年前积压的订单做完后,刘利的制衣厂订单量锐减。工位没坐满,只有6个工人,负责把布料缝合成衣。刘利和丈夫也参与到制衣工序里,熨烫,锁边,剪线头,打包装,和工人们组成一条完整的制衣流水线。
这些天,刘利听到有制衣厂老板找社区哭诉:去年贷款买厂,还没开工便遇到年底疫情,“花几十万就在厂里睡了两个月”,刚准备复工,就收到要拆迁的消息。
目前,刘利还未搬走,“现在还没拆到我这里,可以再拖一下。”
陈敏的情况与刘利相似。她的工厂位于鹭江51号工业区的一个顶层,是一个200平米的铁皮厂。从3月1日改到4月1日,最后落实到5月1日,社区给陈敏下了三次搬迁的书面通知。
三个月前,黄仁的厂子已经被拆了,那时他还在湖北老家,没接到通知。二月初,他从老家返回时,工厂的机器已落在一片废墟里。他是第一批被拆厂的租户。
2019年,黄仁全家一起凑了60万,从熟人手中接来了这个300平米的铁皮制衣厂。生意好时,厂里有10个固定工人,偶尔还需再招一些散工。制衣厂是全家的心血,他将湖北天门的父母妻儿接来广州,一起打理生意。
“刚开始零零散散拆了几家,(我)以为只是走一个形式,没想到这次都要拆。”他连夜卖掉厂里50台制衣机器,当初花了近20万购置的机器,只卖了不到5万,“像卖白菜一样”。
厂子没了,他打电话告诉妻子不用过来了,自己先留在康乐附近的大塘村做散工,顺便观望一下行情。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做回老板。
3月5日凌晨12点,他收到了那一天的薪水,340元,他在微信上继续问老板,“明天还有活儿吗?”

康乐村里正在招工的老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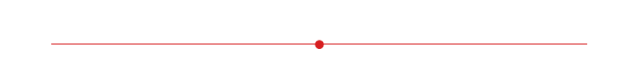
从城中村到“湖北村”
早上8点,鹭江南约大街上挤满人群和电动车。工人们侧身在人群中穿行,交警站在街的尽头,用喇叭督促着街口的车和人,提醒人群不要逗留。
这里是康鹭片区的招工大街,每天早上,制衣厂的老板在此招工,散工们聚集于此,寻找一天的生计。
订单多、缺人手时,王芳也会去街上招散工。和这里大多数小老板一样,她也是从制衣工开始,一步步开起了自己的厂。
老家在湖北天门,家里一亩五分薄地难以维持生计。2004年,16岁的王芳去武汉一个制衣厂当学徒,希望学个手艺。2005年,在亲戚的带领下,王芳和几个同龄姐妹来到广州康乐村,在堂嫂厂里当制衣工。那时,康乐村的房子只有一两层,村里很多地方还是农田。
2005年,广州纺织业因外贸出口权的放开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同年10月,随着广州国际轻纺城建成,中大布匹市场逐渐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纺织品交易市场,成衣加工、仓库存储等下游产业也随之跟进,其范围延伸到康乐村、鹭江村,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服装产业链。
如今,电动车是康鹭片区最常见的运输工具,一辆辆电动车载着辅料、配件、布匹,穿梭于制衣厂与中大布匹市场之间。而在陈敏的记忆里,十几年前的鹭江村,遍地都是脚踏三轮车。那时,她随亲戚来鹭江村做流水工,相比于老家荆州,她觉得这里“经济活一点”,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
“灵活变通”是康鹭制衣业的生意逻辑。靠着紧密的乡缘关系,湖北老乡一个带一个,来到制衣村打工、赚钱、开厂。在康鹭,档口客户与制衣厂、老板与工人之间通常没有正式合同,客户收货后再付款,若无法及时结清货款,制衣厂老板也会宽限几天,但工人的工资要按时发放。这种“信任”维系着康鹭制衣业上下游的合作关系,制衣厂也在这片土壤上野蛮生长。
2013年,黄仁从老家天门来到康乐村时,在表哥的厂里当制衣工。那时,表哥刚开厂,赶上了制衣村生意红火的时期,“每次客户下订单能下几万件,四五十人的制衣厂一年能赚两三百万”,黄仁说。2017年,开厂第四年,表哥在广州珠江新城买了房。
同乡亲友开厂后的巨大利润激励着制衣工。“每个工人都想早点买厂,多赚点钱”,王芳回想最初打工的日子:噪音、灰尘、刺眼的白炽灯、从早到晚的高强度做工、枯燥的流水作业……偶尔让她感到兴奋的时刻,是下班后和丈夫回到那个不足10平米的出租房里,两人头挨着头,在本子上记下自己还差多少钱才能买厂,盘算着买厂时可以向哪个亲戚借一点钱。
2016年末,两人拼拼凑凑了24万,从别人手中盘下了那间150平米的厂房。
外乡人的涌入也重塑着康鹭片区的形貌与生态。在康乐东约南大街上,不到300米的距离,就有至少四五家热干面、监利美食等湖北地方餐馆。
生活设施的完善让这里的湖北人几乎“足不出村”。来广州18年,王芳听不懂粤语,除了房东,她几乎不认识本地人。但她熟悉康鹭的每一条街道,知道哪家档口的家乡小炒好吃,清楚同村老乡在哪条街、哪栋楼里开厂。平日休息时,几个老乡约着在厂里打麻将、在路边吃宵夜。18年来,她的生活以制衣厂为圆心,很少延伸至康鹭以外的广州市区。
陈敏曾短暂离开过康鹭,转行做糕点。“在别的地方打工,走在街上,全是陌生的面孔”,最终,她再次回到了“湖北村”的制衣行业。如今搬迁在即,她舍不得康鹭,“尽管环境不好,但我们都把这当第二故乡。”
3月6日下午4点,在买菜的路上,王芳看见鹭江西街缓慢开进一辆消防车,街边的治安人员拉起警戒线,驱散人群。“有时这里发生火灾,消防车比较难开进来,这应该也是治理原因”,王芳猜测道。

康鹭片区制衣厂老板们在“诚寻客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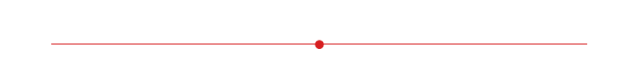
靠“运气”吃饭
康鹭片区的制衣业几乎处于整个制衣产业链中最被动的位置。城中村的制衣厂不做设计开发,也没有能力面向消费市场进行直销。档口客户找来,他们就接单加工,制衣厂的生意好坏,很大程度上依靠档口与电商客户。
在刘利看来,开厂很多时候靠“运气”吃饭,而“运气”主要指客户的生意好坏。
开厂9年,刘利觉得自己生意最好的一年是2021年——她的一名客户做抖音直播,“那年做抖音直播都赚到钱了,往后做(抖音)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生意也越来越难做。”
在采访中,有客户表示,自己在疫情冲击下从实体店转型做直播带货,但在头部主播“量大价低”的冲击下,她始终掌握不到带货的流量密码,新款开发又意味着更大的成本投入和被仿冒的风险,“我们根本没有利润。”
而在康鹭片区,因为办厂不需要技术创新门槛,村里的制衣厂日趋增多,同质化竞争也日益激烈。“你不做的话别人做,你报20块,别人报18块就可以做”,王芳说。
华南师范大学夏丽丽等人2012年发表的研究显示,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具有规模小、技术创新需求低、加入门槛低等特点。在其调研的康鹭片区422家制衣企业中,有92.9%的企业就业人数小于40人,企业年产值主要集中在10-50万之间。在技术创新方面,86.5%的企业完全没有产品的技术研发工作。
上述研究还提到,在康乐村,新企业不断涌现的同时,每年均有一批企业因利润过低、加工量不足被迫关闭。在康乐村厂房转让的信息栏处,“靓厂转让”的告示每天都在更新。黄仁说,因为赚不到钱,曾一起开厂的老乡,有些已经卖厂重回老家。
而靠“信任”发展起来的生意网络,也逐渐成为掣肘制衣厂盈利的因素。出于人情和维系客户的需要,老板们会以极低的利润为客户加工。客户生意不好时,王芳的加工费每件会被压低一两块,而为了留住客户,她只能答应。由于没有设计、销售能力,制衣厂老板在客户面前几乎没有议价空间。
因为没有固定合同,制衣厂老板也会遇到客户延迟付款,甚至拖欠货款的情况。刘利曾因客户的淘宝店倒闭被拖欠了十几万货款,断断续续还了两三年才结清。“但我们给工人的钱是一天都不能拖的。”
现在的黄仁已不再开厂,但仍有以前客户拖欠的近30万货款未收回,“不是故意不给,他们可能也有货积压卖不出去”,黄仁说。
此外,日益上涨的房租成本以及人工成本也成为制衣厂主们的压力。在采访中,一位制衣厂老板2010年从湖北荆州来鹭江开厂,那时200平方的厂房每月租金5300元,而现在,租金涨至17000元。工人价格亦是如此,“以前工人每月2000块都给做,现在前面要加个‘1’”,这位制衣厂老板说。
这些压力在疫情下被放大。
以往生意好时,刘利的制衣厂能从开年一直忙到六月,几乎无休,每天出货七八百件。而现在,仅开工一个月,制衣厂就陷入一种断续的停滞里,偶尔接到一两百件零散的订单。黄仁曾经的制衣厂也是如此,2020年及2022年,他共亏损了40多万。
疫情也暴露了城中村一直以来的治理难题:城中村产业的高度聚集,一平方公里的人口数超过10万,而广州市2022年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530人。
康鹭片区内“握手楼”密布,小街窄巷多,大量人口汇聚在狭小的居住环境内。去年10月,成为广州疫情风暴中心后,康鹭片区的产业转移已迫在眉睫。

康鹭片区的握手楼
今年1月28日,凤阳街道办事处发布的《致康乐鹭江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片区将有序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彻底解决城中村基础设施破旧环境脏乱差、隐患丛生等顽疾;在片区产业形态引导方面,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梯度有序转移,发展数字时尚、创意设计等业态。
而早在2019年,广州政府就提出引导中大布匹市场物流、加工等产业向80公里外的清远市转移。2022年11月30日,广东省湖北商会发布通知,组织湖北籍服装企业主考察清远产业转移园。方案提到,广州拟将清远作为服装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2023年1月31日,广清纺织服装产业园企业集体开业仪式在清远举行,产业有序转移园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000亩,全面建成后能承接企业近10000家。
鹭江村外的街头,在大年初八后的半个月里,每天都能看到清远服装产业园前来接人参观的大巴车。大巴的横幅上写着,“广州北”“科技城”“大量招聘裁缝工”“8000-12000元/月”。大巴车常常坐不满,招工人员曾表示,本只打算在年后第一周免费接送参观,但因为没有招到足够的工人,于是计划再延长一周。
提起清远,刘利摇了摇头,她不会把厂子搬去那里。一方面,清远的配套产业不齐全。制衣工序复杂,往往不是一家制衣厂能包揽的,除常规加工外,印花、烫钻、牛仔洗水等上下游工序,都分布在康乐鹭江片区周围,最近的甚至就在楼下。需要时,最多只需半天就可以把衣服送去再加工。与之相比,清远目前的配套工序并不完善。
另一方面,比起康鹭片区,清远在中大布匹市场80公里之外,距离原料地及下游的批发档口距离都远。搬去清远,难以保证此前的出货速度,而速度,一直是康鹭村制衣厂最大的竞争力。“早上拿到布料,24小时我们就能把衣服发到档口;搬到清远,拿布料时间就要两天”,刘利说。
一位中大布匹市场的资深从业人士表示,清远的有序转移园很难承接康鹭的制衣小作坊,“它所承接的是比较大型的制造企业,不是面向批发型市场的康鹭片区。”该从业人士进一步解释道,很多位于中大布匹市场的商户不仅在布匹市场有自己的布料销售点,同时也在珠三角、浙江、福建等地拥有制衣工厂,涉及布料销售、设计、加工多个环节,“这些工厂少则几千平方,多则几万平方,清远承接的是这样体量的工厂。”
对于广州与清远纺织业的未来发展与分工,广清两地已有明确规划。今年1月13日,清远市发改局发布《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广州与清远的定位,提出“广州总部+清远基地”与“广州研发+清远智造”,其中广州聚焦高端时尚,清远聚焦专业特色。
但无论是研发还是智造,康鹭距离这些都太远了。

陈敏坐在隔壁已搬空的制衣厂门口,寻找新的厂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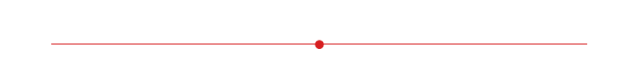
“不继续干这行又能做什么呢?”
城中村治理与产业转移对广州来说势在必行,但对刘利来说,“产业转移”这种词汇太大太抽象,离她的生活很远,她担忧的是:如果继续开厂,低楼层要更高的转让费与租金,重新盘下一个180平米的厂要花费近50万,她和丈夫无力拿出这么多钱。3月1日,刘利更新了一条短视频,“做了九年的厂今天接到了(拆迁)通知,人生能搞几个50万?” 现在,她仍在是否买厂的决策中举棋不定。
在交付新厂定金时,王芳也有过犹豫,厂房转让费要48万,她问丈夫,要不要再多考虑一下?“再考虑,好的厂子都被别人买走了,到时候更贵。”丈夫说。凌晨,王芳交完5万定金,她发了一条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希望是个好的开始,加油!加油!”
如今,王芳已搬进新的厂房,新厂位于二楼,不是违建。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制衣村待多久。
王芳觉得,拆违只是康鹭片区命运转折的开始。“他们说这里人员太密集了,要改造。现在只拆顶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都拆了。”买厂花费的资金不菲,对她来说已是全部积蓄。她希望自己运气能好一点,祈祷着康鹭制衣村能再坚持两年,至少把买厂的钱赚回来。
陈敏坐在工厂楼梯间的布料上,反复念叨自己“运气不好”,觉得那些没租“铁皮房”开厂的人很幸运。她并不知道,早在2021年公布的《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康乐村、鹭江村)更新改造项目公开选择合作企业公告》中,康鹭片区的旧改项目就已被提上日程,改造方式为“旧村庄全面改造”。她小心翼翼地追问,“这里两三年内会全部拆除吗?”
赵成的工厂在陈敏的楼下,他是陈敏口中的“幸运儿”。早在10年前,他就听到过城中村改造的风声,“挪是肯定会挪,但不知道什么时候”。2021年,房东开始将租房合同从“三年一签”改为“一年一签”,他打消了原本想在鹭江村继续扩厂的想法。“风险太大了,假如50万花进去(扩厂),不知道这里什么时候就不能做了。”
对于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能否存续的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在采访时说,康鹭片区的“根”就在中大布匹市场,“因为中大布匹市场的吸引,小型制衣厂才会在这里发展形成,搬往清远很可能无法生存,所以目前更可能的情况是政府只能向周边驱散它,而不能消灭它。”
无论是向周边迁移还是往清远转移,无论成功与否,康鹭片区既往的“辉煌”似乎都难以再延续。
王芳发现,厂里的工人已没有在此买厂、当老板的打算,生意不稳、政策难料,如今已难以复刻十几年前的造富神话。现在还在寻觅厂房信息的,大多是和她一样被拆违的制衣厂老板,“十几岁就出来学手艺、做衣服,如今上有老下有小,不继续干这行又能做什么呢?”
在她搬到新厂的半个月后,原厂被彻底拆除,加盖的铁皮被掀掉,只剩一副空空的铁架。
每到下午,康乐村的街边还会聚集着招揽客户的制衣厂老板们,他们支上写着“诚招客户”的小黑板,三三两两地坐在街边,一直等到黄昏。“一直没有客户,再这样下去要回家种地了。”一位一无所获的老板说。
对于很多制衣厂老板来说,这里像是他们在湖北之外的第二个家,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开厂后,黄仁将父母接来广州,将儿子转学到城中村内的康乐小学。2017年夏天,他带着妻儿登上广州地标”小蛮腰“,那是他来广州的四年里第一次参观它。从塔上向下望去,闪亮繁华的广州夜景让他兴奋,他抱着儿子,感叹这座城市发展得如此之好,他想:什么时候在这儿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就好了。现在,厂子没了,孩子转学回了老家。他不知何时才能再把家人接来,像从前那样,在广州团聚。

康乐村一家打印店门口的“靓厂转让”的告示
刘利和丈夫仍在四处寻找合适的厂房。在康乐村一个不足两平方米的打印店门口,聚集了十几个“看厂”的老板,这是康乐村信息流通量最大的地方。一张张红色、亮黄色的荧光纸上印着每天更新的厂房转让信息,它们被贴在门口,像一条条彩色门帘。
刘利的丈夫驻足在打印店门口,看着眼前这些“靓厂转让”的告示,认真比对价格,记下关键的位置信息。人群中,他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这么着急买厂,你弄明白政策了吗,这次又能开多久?”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芳、刘利、黄仁、陈敏、赵成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