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野猪猎人决定金盆洗手(一个野猪)
时间:2023-08-04人气:作者: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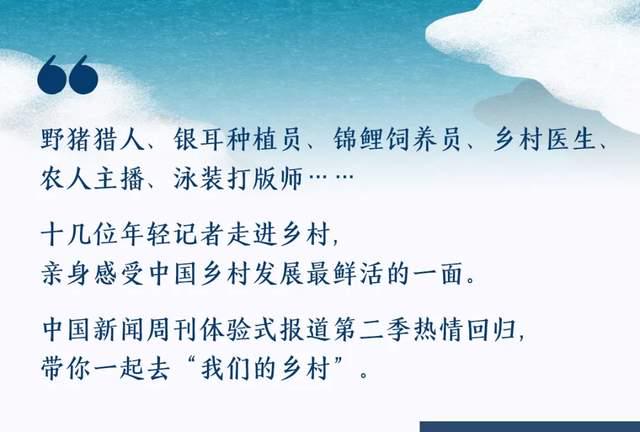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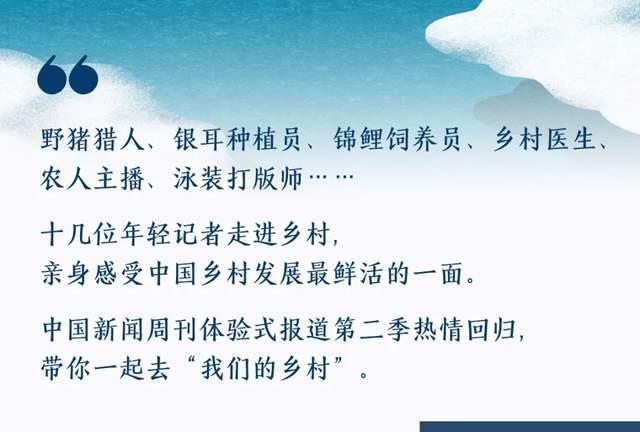
题记
6月中的一天,宁夏固原某县,凌晨2点,室外温度5摄氏度。
血红色的皮卡车悄悄靠在山道边停下,轰鸣的引擎声音瞬间熄灭,车厢内外一片漆黑,只有无人机屏幕和三支快要燃尽的香烟闪烁着亮光。
“走,放狗!”老吴狠狠捻灭烟头,跳下车前他叮嘱我:
“胖子,山上根本没有路,你跟不上就别硬来,狗比你能跑!”老吴说话声音非常轻,是因为害怕担心声音太大吓跑山上目标。
等我整理好从皮卡车上挪下来,人和狗都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的山林中独自凌乱。
人猪冲突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记者,人兽冲突是我持续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青藏高原的流浪藏獒,还是南京城内流窜的“网红猴”,或是上海社区中出现的貉,都曾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有一种动物,我关注它的时间最长,那就是野猪。
近年来,随着全国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系列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长。由于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使得部分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兽冲突。
几乎每年春种和秋收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关于野猪下山祸害农田的新闻,被野猪祸害过的农户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
但事实上,由于野猪被收录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中,所以即便是野猪肆虐糟蹋庄家、林地,普通农户和百姓也无法捕杀,只能驱散,这就造成了人猪冲突的不断升级。
我前往的宁夏固原某县,绝大部分当地人依靠种地为生。因为缺水,农作物都是靠天吃饭。
“有时好不容易下了雨,雨停了猪来了,一年都白干了。”
说这话的老吴和我同岁,今年本命年,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不善言辞,但有问必答。
我俩之间的对话经常因为没有话题而被迫终止,但他只是笑笑看着我,从不主动打破沉默。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正是在那年,老吴成为了一名有证的合法“野猪猎人”。

野猪。图/中新社 余昌军
此前有媒体报道,陕西渭南林业局曾以2500元/头的价格悬赏猎杀野猪,需要合法的猎人通过合法的方式清除猪害。老吴看到消息盘算后认为并不划算,因为固原当地给他的价格是1850元/头,算上差旅费,渭南开出的价码并不高。
当地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告诉老吴,今年的指标是多少,老吴则会严格按照指标进行猎杀,猎杀后的野猪将送到当地林业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老吴有两个伙伴,一个是从黑龙江来投靠他的老宇,另一个是同乡老刀。三人分工合作,老刀负责用无人机锁定目标,老吴和老宇则负责放狗补刀,这已经是抓猪小组最精简的配置了。
电话中得知我要去和他一起抓猪,老吴犹豫了一下,“狗病了,要不缓两天?”
在我再三坚持下,老吴松了口,“你来吧,来了正好帮我给狗打针。”
24小时后,我辗转1500公里,站到了老吴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下了结论:
“兄弟呀,你这个身材,抓不了猪。你200多斤肉在山上跟着我一起跑,狗再把你当猪咬了,我还得给你打针。”老吴没有开玩笑,相比起抓野猪,从外貌上看,吃猪肉更像是我的特长。
“走吧,先看看狗去,想抓猪,先喂狗。”老吴把我塞上了他的皮卡车。
没名字的狗
县城不大,皮卡车开到了一处山坡上的平房前,平房外的地面上溜达着五六条狗,巨大的狗吠声隔着车窗就能听见。
“走!走!都给我进去!”老宇将平房的铁门打开,里面是大约80平米的院子,旁边有两间平房。

老吴的猎犬。图/胡克非
目视所及,院内大约有近40条狗,见到有人前来,它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
“你别怕它们,它们都不咬人。”老吴将铁门带上,随后径直走进了房间准备给狗的餐食。老宇则在另一间房内准备给狗打针的药和针头,这是他刚去诊所买的,花了大约2000块钱。
此时,只有我一个人类,被近40条狗团团围住。我开始盘算我这200多斤肉,够40条狗吃多久。
我叫不出这些狗的品种,它们和我想象中的“猎手”截然不同,并不是头颈四肢细长的细狗,也不是在短视频中常刷到的“世界猛犬”,外观上更接近于日常概念中的农村土狗,健壮且充满活力。
一时间很难把它们与老吴口中的“战士”联想在一起。对于我这个陌生闯入者,它们的好奇心使得它们频繁上前与我接触,仿佛是要记住我的样子和气味。
我蹲下来用手触碰了几条狗的鼻子尖,湿湿的,应该是很健康。
老吴拎着狗食走过来,几乎是一瞬间,围住我的狗群便抛弃了我,拥抱了狗食槽子。

“汪汪队”开饭。图/胡克非
狗食的样貌很难用文字形容,那是一种容纳了牛肉、鸡肉、玉米、狗粮、蔬菜、谷物的混合物,通过大铁锅煮熟后,呈现出一种青绿色半固体的状态。如果不是狗们正在吃,我会以为这些东西是农村砌墙用的水泥。
狗太多,多到甚至绝大部分没有名字。老吴告诉我经常会有狗“战死”,平时也会病死。所以只有抓野猪立过“战功”的狗才会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大狗娃”和“二狗娃”。
我依稀理解了老吴不给狗起名字的原因,是希望尽量避免自己和狗产生更多的感情。
老吴衡量“战友”的标准并非相貌和性格,而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
猎犬们分为头狗和帮狗,头狗搜索并围堵野猪,帮狗负责对野猪发动攻击。老吴告诉我,我口中的那些浑身细长的狗,是用于追兔子的,“那种狗根本抓不了猪。”
汪汪队立大功
西北的夏天和北京差异很大,白天太阳出来后,温度迅速升高,午时可达近30度,但在阴凉下仍然干燥凉爽。
一旦太阳落山,因为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县城的温度便会骤降。太阳落山后1个小时,温度便会下降至15度左右。而在深夜的山上,温度会趋近于零度。
上山前,我们再次回到了狗场,老吴掏出了20个GPS项圈,选择出了20条狗,为它们依次戴上项圈,并且记下每一条狗对应GPS的哪个波段,这决定了抓猪行动后,能否把狗平安收回。
野猪绝非愚蠢的动物,在温度升高的白天,它们极少下山活动,一个原因是过高的气温会消耗更多的体力,另一个原因则是白天农户的警惕性更高,下山活动危险性极大,所以在夏天,野猪们几乎都会选择在后半夜下山进食,目的地多为山下农户的田地。
农户们仿佛已经习惯了野猪深夜到访,只有少数农户悬挂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一些野兽的声音试图驱散野猪,那声音在深夜山野中显得格外诡异。
老宇摇下皮卡的车窗对我说:“你听,这些玩意能吓唬谁?野猪第一次听或许会警觉,听习惯了就跟‘开饭了’一个意思。”
抓猪的流程并不复杂,简单可以分为:放无人机找猪、放狗追猪、补刀、收狗这四个流程。
老吴驾驶皮卡,副驾驶的老刀则在山间放下无人机,随后用无人机在较高的区域搜寻野猪的位置,要注意无人机的高度,太高看不清楚猪在哪,太低则会因为无人机的声音将猪吓跑。
我和老宇挤在皮卡后排,老宇正在擦拭他的刀。那是一柄刀刃长约30cm的短刀,妥妥的管制刀具。平时刀被收在刀鞘中,当狗咬到猪后,它将作为最后了断猪的工具。
足够长才可直达心窝,足够锋利才能一击毙命。我推开刀鞘,可以清晰地看见刀刃上的血迹。
“这血是上礼拜杀的那头猪,足足有300多斤。”老宇指着血迹对我说,“出刀要又快又狠,不然一刀没捅死,它跳起来就可能伤人,还可能伤狗,我们都被猪伤过。”
老刀一连放置了几次无人机,都没有看到猪的身影。看出了我沮丧的老吴对我说:“你听说过猎人是十猎九空么?但我们不同,我们是十猎一空,你要相信我。”
突然,老刀紧张了起来,老吴立刻停下了车。我们几个脑袋都凑到了副驾驶的老刀身边。在屏幕上发现了一个小白点,三人均表示,那就是猪,正在半山腰的农田里找东西吃。

无人机镜头下猎狗追逐野猪画面。图/胡克非
老宇手指着白点说出了一些信息:猪不大、100多斤、雄性、大约两岁半。
我大惑不解,“你是怎么看着白点推算这猪的重量和年龄?”
“你看这高度、再看参照物农田,就可以判断这个猪有多大。雌性一般群体行动,带小崽,雄性则单独出没。100多斤的猪大概两岁多一点。这都是经验,你们记者哪知道这些。”老宇说完继续摩挲着刀鞘。
锁定目标后便是放狗,要精准地把狗放在距离猪最近的位置,以便让狗可以用最短的距离追上目标,从而击杀。
我跟着老宇和老吴一起放狗,20条狗跟随着二狗娃呼啸着进入了山林。
黑暗中,我啥也看不见,只能跟着老吴和老宇的脚步走,崎岖复杂的山路在他俩脚下就像是平地,我甚至需要四肢并用才能通过,很快我就听不到他们了。
正当我迷茫不知所措时,狗吠声大起,我想起了老吴的玩笑,“坏了,狗娃们不是把我当猪了吧?”
15秒后,老吴出现在我面前,手里一手拎着一条狗,“收工,狗跑反了,猪跑了。”
经过第一次失败后,不到20分钟后,一个白点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老吴和老宇带着狗冲进山林不久,我们便收获了这天的第一个猎物。

捕获到的野猪。图/胡克非
我帮着他们用绳子将猪拖出山林,可以看到,猪已经死透了,胸口有明显的一个刀口。
抓到猪之后,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收狗。
抓猪10分钟,收狗收半宿
虽然有头狗带队,但是下到山林后,狗的行动是随机性很大的,狗是循着猪的味道进行追踪,嗅觉好的狗,可以闻到距离放狗点一公里外的猪味。
有时抓到了猪,但狗又闻到了其他猪的味道,继续追踪,就会出现狗没收回来的情况。
老吴告诉我干抓猪这行,丢狗是常事,有的时候一两个月才能找回来。
狗脖子上有GPS项圈,我们手里有追踪器,每条狗的信息都会出现在追踪器上,但在山林间GPS的信号并不稳定,每一条狗所在的位置也不固定。
我们大约在凌晨2点左右结束了抓猪行动,之所以草草结束,是为了照顾我,他们决定收工。但还有大约10条狗没有归队,所以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便开始了漫山遍野地找狗。
皮卡车几乎无视地形在山间穿行,皮卡的底盘不时传出和石块林地亲密接触的声音,听得我格外心疼,为了防止睡着,我决定和老吴聊天,但他其实并不需要和我聊天便可以集中注意力开车。
“这车这么开,能用多久?”
“这车抓猪一年就完蛋。”
“一年抓猪成本:一辆皮卡,大约12万元人民币。”我在笔记本中记下。随后我快速计算,杀一头野猪补助1850元,大约杀65头猪可以买一辆皮卡。
“一条狗大概多少钱?”我算完车钱开始算狗钱。
“这些狗都是我们自己繁育的,成本低一些,如果是购买的话,像二狗娃这样的抓猪老手,大概要卖10万元,其他的普通狗,也大概在1500元到3000元不等,好一点的上万。这些狗一个月大约要吃掉2500元,还不包括生病和战死的损失。”老吴说。
“你再算,这个无人机45000元,热成像仪2万元,再加上这些GPS定位线圈和仪器,也得小十万块钱。”
我边听边往本上记,“合着你抓这东西不赚钱啊!”
“谁跟你说赚钱了?赚钱干这个干嘛啊?”老吴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
“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了!”老吴举着追踪器边冲一团漆黑的山林呼喊,边吹响口哨,大概5分钟后,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最后一条狗,叫黑娃。
返回狗场时,已经是凌晨4点,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几人协力把捕获的野猪丢进狗场的院中,老宇熟练地将猪肚皮划开,掏出内脏,随后便是狗娃们的大型吃播现场,干活的和没干活的狗一拥而上,把我们刚打到的战利品瓜分一空。
很快,一头100多斤的野猪就只剩下一张猪皮、几根骨架和一整个猪头。
这些剩下的东西,都要用编织袋装好,它们是去林业部门换1850元补助的凭证。
干完今年就不干了
离开县城前,老吴喊我吃饭。
几天来,我感受到了西北县城离谱的物价,一碗过油肉拌面要30元,几乎和北京的价格持平。老吴说,当地人的平均月薪大约在3500元左右,物价一直就是这么高,所以大部分人家平日是不出来吃饭的。
“因为出来吃饭的人少,饭店价格就越来越贵。”老吴说。
老吴曾在县城经营一家水暖店,家里有两个娃,平时都是妻子在照顾,疫情期间,水暖店的生意黄了,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全职的野猪猎人。
老宇已经是退休的年纪,投奔老吴是为了玩,并非为了钱。
老刀最年轻,但却已是三个娃的父亲,因为贪玩,和老吴两人混在了一起,算是团队中的技术人才。
说到娃,老吴显得有些愧疚,“人家娃娃说起自己的爸爸都很骄傲,但是我家娃娃每次说到自己的爸爸是放狗杀猪的,我都有点难过,这听上去不怎么光彩,对吧?”
老吴明白,野猪猎人终归是玩,并不是个职业。抓到野猪可以从林业部门换到补助,但是对于被救助的农户老吴从来分文不取。
三人告诉我,自己并不是喜欢抓猪,而是喜欢养猎狗,抓猪是玩狗的衍生产物。但玩狗毕竟是一个成本巨大,并且抛家舍业的事情。三人都表示,干完今年就不再干了。
老吴决定接下来做点正经营生,让家里人的生活好起来。
“野猪是打不完的,但是人就活这么一辈子,大老爷们不能不管家。”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去年,老吴在某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并且开通了直播,无人机的画面可以连接手机直播,所有关注账号的用户都可以看到抓猪的“现场直播”。
在短视频平台,老吴卖出了一些设备和狗,还为一些无人机和热成像仪的厂家做代理,也可以赚一部分佣金,但对于养狗抓猪的开销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短视频给老吴带来了被“追捧”的感觉,部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们在西北这个偏远的地方,从来没去过大城市,但是短视频让我们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也让更远的地方的人们看到了我们。”
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的流量,也让老吴开始担忧——不少没有合法资质和手续的偷猎者,为了流量开始上山抓猪,为了流量也会在抓猪的过程中采取一些危险或者不合法的方式,甚至还会抓到其他野生动物。
不少直播抓猪的人,已经偏离了最初护农的目的,变成了单纯地狩猎和换取流量。
因为没有合法的手续,抓到的猪也不去做无害化处理,这些都会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劣币正在驱逐良币,这就是流量带来的反作用。
我明白,老吴这里或许是流量最后抵达的地方,所以人们对于流量没有任何抵抗力。
老吴掏出手机给我看,在自己的粉丝群中,有不少人催更。“什么时候杀猪?晚上杀不?哥几个今儿晚上干一头300斤的!”
“这些粉丝是真心想帮助农民的么?”老吴反问我,但我却没有答案。
6月30日,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
已经回到北京的我给老吴转发了消息,他很快回复我:“看到了,但野猪也不能乱杀。”
我追问:“政策改变了,你明年还杀猪不?”
老吴的回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不了。”
(应受访者要求,老吴、老宇、老刀均为化名)
作者:胡克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