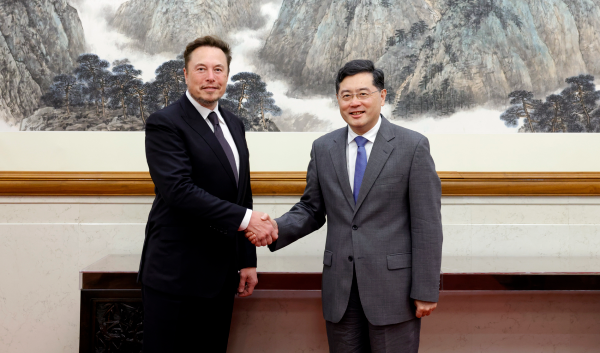没有完成的攀登 没有完成的攀登怎么办
时间:2023-05-31人气:作者:未知

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方救人是什么感受?
“氧气只有海平面的27%,呼吸变得困难。”“连打开一个水壶喝水都费劲。”54岁的谢如祥这样形容。
5月18日深夜,在海拔8450米、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仅四百米处,他和39岁的范江涛决定终止登山,救援一名倒在路边的登山者。他们及夏尔巴向导总计花费了四个小时,下撤五百米,将遇险者运送到最近的营地。
范江涛是湖南省登山队领队、湖南登山运动协会副主席、湖南省高山专业委员会主任。谢如祥曾任北大山鹰社登山队队长,现是湖南省登山队队员。从2016年起,范江涛就梦想着登顶珠峰,谢如祥则是在2018年定下这个目标。
多年的准备与等待后,他们决定在与终点咫尺间放弃登顶,只用了几分钟。

湖南省登山队合影,右一为范江涛,前排坐下者为谢如祥。受访者供图
一
5月18日是登山的绝佳天气,范江涛回忆,“几乎没有一点风。”根据当地夏尔巴向导提供的天气预报,这种好天会持续到19日早上。
傍晚五点半,范江涛和另外两位队友以及夏尔巴向导,从海拔7950米的珠峰C4营地出发,做最后九百米的冲顶。六点半,谢如祥出发。
一行人负重许多:连体衣、头巾、帽子、围巾、高山靴、双层手套、1.5升开水和氧气面罩是生存必需品。要攀登,还要带上升器、下降器、冰镐、冰爪等技术装备。谢如祥说,一个氧气瓶就3.5公斤,身上的总负重超10公斤。
但他们行进顺畅。晚上8点多,他们就到达了被称为黄带的冰岩混合地带最上沿,且都觉得体能充沛。如按计划,他们将在当地时间第二天凌晨三点前登顶。
范江涛带了一部卫星电话,“我甚至在想,登顶后,国内不知道天亮了没有?我第一个报喜电话要打给谁?”
夜晚的珠峰黑透了,只有头灯照射的地方有些能见度。晚上8点20分左右,范江涛照到前方路上卧倒着一个人,穿着火红的连体衣,蜷缩在路绳的右侧。

谢如祥(左)和夏尔巴向导。受访者供图
范江涛又看了一眼手表,显示海拔8450米。“按业内的惯例,海拔8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可以不救人坦然走过的。因为在这高度,救人很难,而且容易把自己也搭进去。”他与队友也决定继续前行。
倒地遇险者的锁扣仍系着路绳,范江涛等人要前进,就必须解锁安全绳,绕过遇险者,再扣上安全绳。等待队友们解锁、扣锁的时候,范江涛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发现遇险者脸上覆盖薄冰,身穿的连体衣已大面积破损。左手裸露,已冻得发黑,右手戴着薄抓绒手套,整个人都在颤抖。
他问遇险者,你是中国人吗?对方没有回应。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对方轻轻说,自己姓刘。他这才认出了她——都是登山爱好者,他在日常拉练时常与她打照面。再询问,得知她没有向所属登山队报备,自行找了登山公司及夏尔巴向导来攀登珠峰。
一旁的夏尔巴向导提醒他,此人救不了了,应该继续向上。
“第一次是被说动了的。”范江涛绕过了刘女士,又随着夏尔巴往前走了二十来米。走着走着,他想起一个人。
前一天,也就是5月17日,第一批登顶成功的队友回到C4营地,带来一个消息。他们在山上看到一个登山者倒地,他们尝试急救,“但没救过来。”看他衣服上的名牌,叫陈学斌。
另一个消息流传在几个相识的登山者之间,随大家一路走到C4营地的、昵称为“木匠”的登山者在冲顶时失联了。
为确定消息,范江涛和队友们满营打听,得知“木匠”就是陈学斌,“一瞬间就特别难过。”范江涛与“木匠”没怎么说过话,但一路同行,又在一个营地生活了几天。“对那个人、那张脸都有印象。”他感慨,“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
晚上8点45分,范江涛停在漆黑的山上,痛苦又纠结:不去救,刘女士的生命或者就像“木匠”一样转瞬即逝。去救,氧气和体能都不可能再供他冲顶。且峰顶就在眼前——一个人一生有多少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机会?
想着想着,他痛哭起来。哭完了,他告诉夏尔巴向导,不登顶了,他要下去救人。
二
范江涛回忆,自己下撤回刘女士身边后,先将她脸部的冰抹掉,给她喂了点热水和巧克力,把自己的羽绒手套和氧气瓶也给了她。
晚上9点左右,刘女士恢复了语言能力,告诉他,自己是前一天上山的,到今天中午,她和随行的夏尔巴向导都没水了。氧气是什么时候耗尽的,她不记得了,糊里糊涂地,手套丢了,夏尔巴向导也不见了。
范江涛没再问什么,与自己的夏尔巴向导一左一右架起刘女士,各自空出一只手扶着安全绳,滑着往山下去。很快,他的手套就磨破了。
下行一百多米后,晚上10点钟时,刘女士再次晕倒。“那会儿我绝望了,我和夏尔巴向导的力气也用得差不多了。”范江涛与夏尔巴向导将刘女士抬到一块较为平坦的石头上,用一段废弃的路绳稳定住。而后他拿出GoPro(移动摄影机),问刘女士是否有话想说给家人,“她还是迷迷瞪瞪的,说没有。”
做好一切准备后,范江涛决定下撤找人施救,往下三十多米后遇到了上山的谢如祥。

湖南省登山队在赶往C2营地,最前者为范江涛。受访者供图
谢如祥回忆,5月18日晚上10点左右,他和夏尔巴向导攀登至8300米的高度,迎面遇到了范江涛。后者喊了句“祥哥”,立刻又哭起来。“他告诉我,在上面碰到遇险的刘女士了,她只有一口气了。”谢如祥说,“他和夏尔巴向导救了很久,但救不动了,很崩溃。”
“在海拔8000多米的地方,救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个位置的氧气只有海平面的27%,呼吸变得困难,停留时间越长,风险就越高。我连打开一个水壶喝水都费劲,再多带一个人下山,会很辛苦,危险系数也增加了。”谢如祥说,“但还好我和夏尔巴向导出发不久,我的体力、氧气和水都只用了大约20%。”
谢如祥决定,让范江涛先在原地休息,他和夏尔巴向导上去探探情况。上行三十多米后,他找到了卧地的刘女士,又喂她喝了些热水。而后,他对夏尔巴向导说,自己放弃登顶了,要救这个人。“夏尔巴向导对此挺不理解的,在登顶珠峰的路上,他看到过很多倒在路边的遇难者。如果救不了,夏尔巴向导也会放弃对方,毕竟保证自身安全是第一位的。但如果不救,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哪怕她遇难了,我也要把她带回营地。”
谢如祥向夏尔巴向导承诺,只要把刘女士送回C4营地,就给他一万美元的奖励。这个队伍里最强壮的夏尔巴向导同意了,卸下背包,背起刘女士。三人下撤,与范江涛会合。
两个夏尔巴向导轮流架着、背着刘女士,范江涛在背后托举,年纪较大的谢如祥则在后面跟着。
路上,谢如祥仍出神地幻想着,把人送到营地后,自己是否可以再次冲顶?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C4营地到峰顶的最后一段路程,两名夏尔巴向导给谢如祥和范江涛各背了三瓶氧气,他们自己也背了一瓶。这些氧气的用量经过严格计算,中途没有任何补给的可能。因此,要想再次登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氧气。且按天气预报,本年的攀登珠峰窗口期在明日就要结束了。
“直到夏尔巴向导叫了我一声,我才回过神来,今年是登不了珠峰了。”谢如祥说。他和范江涛估算,为此次登山,他们各自花费了包括注册费、交通费、向导费、保险费等在内的三十多万元。
时间成本的付出也是巨大的。
早在4月9日,湖南省登山队一行九人就从长沙出发了。他们12日到达加德满都,而后休整,又花费八天时间,从海拔2800米的卢卡拉徒步到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在大本营停留了大半个月,适应高海拔生活,然后开始拉练——从大本营向上经过C1、C2营地,再折返回大本营,等待窗口期的到来。
根据夏尔巴向导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从5月13日开始。5月14日晚上11点半,谢如祥、范江涛等九人从珠峰大本营出发,正式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5月15日,队伍到达海拔6500米的C2营地,5月17日,到达海拔约8000米的C4营地。
C4营地是冲顶前的最后一个扎营点。再往上,他们将经过大雪坡、黄带、阳台、南峰顶和希拉里台阶,然后抵达峰顶。然而,5月18日深夜,为救人,他们最终止步于黄带上沿。
三
连续下撤三个多小时后,5月19日凌晨1点,他们到达C4营地。谢如祥记得,此时气温大概在零下20摄氏度,“穿连体羽绒服都觉得冷。”
他们把刘女士带进一个空帐篷,范江涛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她,并往她脚下塞了一壶热水。
第二天早晨,帐篷顶内侧结了一层呼吸凝成的“雪”。刘女士的精神好了些,醒来后问范、谢两人,自己登顶的照片在哪里?“我感觉她有点像喝‘断片’了,不记得自己遇险和获救的经历,还问我们怎么也在这里。但我觉得,她不记得也是件好事,这或许是段痛苦的回忆。”谢如祥说。而后不久,刘女士就被自己找的登山公司接走了。
湖南省登山队伍是5月19日中午从C4营地离开的,20日下午到达大本营。回到加德满都后,谢如祥在一家酒店又遇见了刘女士,“问候了一下,她说恢复挺好的。”

队员们在C3营地附近的洛子壁攀爬。受访者供图
刘女士回国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被救的经历属实,但“人迷糊了”,提供不了更多细节;对于范、谢的善举,则是“救命之恩,应当感谢”。
这一趟不算圆满的旅行,让范江涛瘦了二十斤。“我们生活在平原的人,到了高海拔地区,做任何事都是在消耗自己的身体,运动系统和消化系统都会受影响。”14日从珠峰大本营出发那天,他的肠胃就闹起不适,多次呕吐。
如影随形的还有无法预判的危险——冰川、冰梯的坍塌都是概率问题。因此,要过冰川时,登山者们往往选择夜晚出发,以避免阳光照射导致的冰川、冰梯的加速融化。
范江涛说,前期拉练时,他们穿过大本营外的昆布冰川,亲眼见到一处冰川在身后一百米处坍塌,扬起的风裹着冰雪扑面而来。“如果我们走得慢一点,可能就随着冰川塌下去了。”下撤回大本营时,又遇到冰川坍塌,这次有个队里的夏尔巴向导掉下去了,所幸被人拉起,没有大碍。
最终,湖南省登山队中,包括随行摄影师在内的三人成功登顶。其余队员因身体不适、氧气不足、夏尔巴向导受伤等状况未能登顶。
“有些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登珠峰。我觉得,人对未知的东西,是有探索的欲望的。其次,经过努力,登上山顶,会很有成就感。重新登山后,我感觉自己又活了起来,变得年轻了。”谢如祥说。
他曾是北京大学山鹰社的登山队队长。1990年,他就带队登上了海拔6178米的青海玉珠峰。后来他一直有登珠峰的想法,但总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2018年,北大成立120周年校庆之际,山鹰社的同学们去登了珠峰。他听说后,“觉得自己的珠峰梦又燃了起来。”
从2019年开始,谢如祥恢复登山训练,陆续登了乞力马扎罗山、玉珠峰和哈巴雪山等。此次未能登顶珠峰,是“没缘分”。他希望未来再去尝试登顶。
范江涛则已经“预定”了明年或后年的春天攀登珠峰。2008年,他在网上看到一个名为“北方的空地”的帖子,里面详述了作者穿越大羌塘无人区的经历。他通宵把帖子看完,从此对徒步、穿越及登山产生向往。2016年,他定下“7+2”(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的登山目标,开始攀登高海拔雪山。
现在,他在长沙经营创业公司,办公室里放着十几张登山证书,“国内海拔五六千米的山基本上爬完了,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最高峰也都爬完了。”珠峰是他的第四站。
此次未能登顶,风景却已经看饱了。他记得爬黄带时,正是傍晚,夕阳下,他身下成片的雪山拉出了一条条长影。“眼前完全没有遮挡,特别壮阔,真正的一览众山小。好像在俯瞰全世界。”
他还有些更感慨的事。从大本营出发前,众人举行了“煨桑”仪式,当地喇嘛也赶来参加。大家向天空抛洒大米,听喇嘛念念有词。他知道,除了祝福的意味,这也是让人们敬畏大山。
5月19日早晨,也是救下人后的第一个早晨,他在帐篷中醒来,看到自己深夜迷迷糊糊抓来的睡袋上,写着“木匠”两个字。那是遇难者陈学斌的睡袋。那瞬间,他百感交集。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吴采倩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