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学校该如何面对学生的死亡(学校出现学生死亡)
时间:2023-12-03人气:作者:佚名

记者/张涵 实习记者/吕一含 安然然 张瀚允
编辑/刘汨

自杀事件后的危机干预不能被忽视 | 电影《阳光普照》
校园发生自杀事件后,可能有超过一百个人会承受不同程度的悲伤。
有人在同学坠楼的地点驻足,不过只让悲伤在心里停留一会儿,因为学习太忙了。而对于更加细腻敏感的人,一个看到女童走失新闻都忍不住担心几天的人来说,同学自杀带来的悲伤可能席卷全部生活。
每当有学生自杀,公众的焦点往往集中在死者本身,与其相关的“悲伤者们”沉默于背后。有研究表明,每次自杀事件会波及到约135人(认识或认同死者的人),不只包括家属和亲历者。无论关系或远或近,目击者、老师或是学生,都可能是需要帮助的人群。
接下来该怎么做,是学校危机预案中的一环。如何识别这些悲伤者?要不要公开哀悼?如何提供心理支援?这些具体的决策背后,是一所学校面对生命的态度。

港中大在学生离世后的通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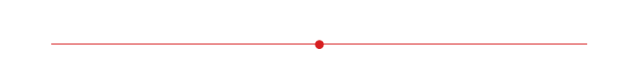
被悲伤波及
2019年10月23日。
出于一些负罪感,陈小丹把朋友自杀的日子记得很清楚。
那是大一开学不久,下课后她像平时一样去洗澡。洗到一半,同学突然找到她,“快点,出事了。”班里一名男生在宿舍留下遗书,不见了。他和陈小丹是高中同学,不久前他们还约定要一起备考英语四级。
陈小丹和同学们去了学校新建好的顶楼上,又设想了很多僻静的地方,但一直找不到人。有同学查看了监控,推测他去了一片树林。
陈小丹和同学正好在附近,他们跑过去,发现一个人影挂在树上。陈小丹打开手电筒,心里默念着:千万别是他。光一照过去,许多女生都吓哭了。陈小丹大脑一片空白,和其他人冲上前去。有人爬上树去把绳子解开,大家不知道他窒息多久了,几个同学轮流给他做人工呼吸。
后来,班长随救护车把那名男生送去了医院。到场的老师让大家早点回宿舍,不要再讨论这件事。那一夜,许多在场的人都没睡好。陈小丹不断刷着手机里的资讯,搜索着“上吊多久才会死亡”。
陈小丹还是失去了她的朋友。随后的一个月,她上课没法集中注意力,“脑子嗡嗡响”。她开始怕黑,怕去树多的地方。睡觉不敢朝向外侧,怕睁眼就看见令人害怕的景象。她也常常梦到那天晚上,只是结果不同——她在某个地方找到了朋友,他正坐着发呆。
她试图找人倾诉,但父母担心她深陷其中,不让多说。告诉好友,她们都很震惊,但没有类似的经历,一时不知怎么安慰她。有高中同学听说后,一直追问那位同学是怎么走的,还说“为啥没看好他”。陈小丹很受伤,再有人来问,她只说自己不清楚。
那段时间,陈小丹上课想哭,吃饭想哭,走路也想哭,看搞笑综艺也开心不起来。她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受到冲击的不止她一个人,一名女生在班级群告诉大家,她去医院确诊了精神疾病,自己之前出现过焦虑等情绪问题,这件事的刺激加重了她的症状。
这是自杀事件发生后常见的情况,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自杀原因和事件本身,而忽略了周边人群受到的影响。研究自杀问题的学者Julie Cerel在一篇论文中将暴露在自杀事件中的个人定义为“任何认识或认同死者的人”,因此受影响的群体不仅包括亲属或亲历者。
她的研究表明,每次自杀事件发生后,会波及到约135人,他们或许需要医疗服务或支援。还有研究提出,学生死亡后,学校工作人员处于应对危机的第一线,但经常没有被视为受影响和需要支持的人,他们是“被遗忘的悲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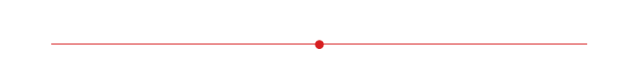
识别“悲伤者”
自杀事件第二天的语文课上,班长带回了那位同学抢救无效的消息。班里哭成一片,课堂没再继续下去。辅导员和校领导到班里安慰大家,安排他们自愿接受心理辅导,也包括和那名男生有联系的其他班同学。
之后的一段时间,还在怀孕的辅导员每天早上都会在班级群发一句问候,“天气冷了注意多添衣”,或是“生命就像花一样”。陈小丹很感动,她不知道辅导员的难过有没有人帮她排解。
近三年,多地教育部门印发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手册,都提到了发生危机事件后,对可能受影响师生的评估和干预计划。比如广东省在2020年3月发布的手册,参考了香港、台湾等地的做法,列举出了几类受影响较大的人群,比如亲历了危机事件或置身现场;与当事人关系密切或存有嫌隙;同一班级、寝室或社团;未必亲历事件或与当事人有密切关联,但个人的脆弱程度较高。手册提出,针对受影响程度由轻到重的学生,学校需分别提供班会课、小组辅导、个别辅导或转介至专业机构等支援。
深圳市宝安区教科院教研员石红梅在论文《当B同学自杀后——学生自杀心理危机干预的案例分析》中,分享了协助处理一起中学学生自杀事件的思路:
“当自杀行为发生,在学校环境中需重点关注几个人群:学生、家长、班主任老师。学生群体包括:看到当时场景的学生;B学生所在班级学生;B学生同寝室的同学;与B学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学生,包括:好朋友、有过冲突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开展活动的伙伴、借过钱(物)的同学等;在心理健康普查中查出有显著心理问题的学生;近期在家庭或学校环境中发生过较大冲突的学生;听到这件事情后情绪起伏比较大的学生;最近有自杀意念的学生。
在所在班级学生自杀的突发事件中,班主任往往在情感方面受到很大冲击。尤其这位班主任老师前一晚还跟 B 学生促膝长谈,并且感觉到学生的状态很不错,谈话激发了学生的希望和学习目标。当事件发生后,班主任老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情绪几乎崩溃。”
想要完整地识别“悲伤者”群体并不容易。浙江省奉化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姜红霞在论文中记录了一次参与干预的经历:2021年3月,本地一所初中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她带领心理危机干预小组成员来到学校,对相关师生的心理状况进行了排摸和评估,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个体辅导、小团体辅导及班级哀伤辅导等。
在事发第六天,学校再次与她联系,希望能为一名情绪反应强烈的初三女生提供辅导。这名女生是自杀学生最好的朋友,但不在同一班级,两人之间的友情只有少数学生知道。在事发当天,她没有异常的表现,第二天又很快请假回家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这名女生被忽略了。
姜红霞总结道:我们应通过多种渠道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当事人的人际关系,同时对于曾有自杀经历的、事发后请假的学生应予以重点关注,而不能仅仅将关注点局限在当事人所在班级以及当前在校的学生中。

自杀事件发生后,人们可能会承受不同程度的悲伤 | 电影《阳光普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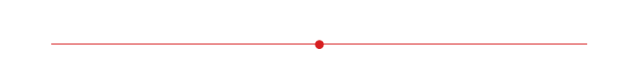
麻木和负罪感,都是悲伤
团体辅导持续了两个小时。十多人围坐在心理咨询室,分享彼此的感受。有人说着说着就哭了,有人相对冷静地分析那位同学之前表现不对劲的地方,还有人说走过那片树林时,感觉他还在那里。陈小丹始终在哭,什么都说不出来。咨询师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变化,希望他们用平和的心态看待这件事。
后来,一些同学逐渐恢复,但她一直陷在悲伤里。陈小丹敏感,容易共情。每次看到负面新闻,都忍不住想象其中人的处境,一直担心着后续。
起初,她怀疑自己是个对朋友冷漠的人。每当提起找到自杀同学的经过,所有人都很震惊:“你咋那么勇,不哭也不跑,要是我早就吓得不敢动了”,陈小丹也开始回忆,当时自己的行为好像过于冷静了。
后来,陈小丹才知道,“麻木”也是悲伤的一种表现。美国精神病学家库伯乐罗斯在1969年提出了“悲伤五阶段”,包含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悲伤五阶段不是线性的,有可能会在一瞬间经历每个阶段,或是不断循环。一般人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接受负面的消息,在否认的时候,有的人会呈现出麻木的反应,不代表内在没有哀伤。
渐渐地,意识到朋友真的离开了,陈小丹陷入了抑郁。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心不起来,在网上查找抑郁症的资料,寻找同样失去朋友的人,根据对方的描述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但依然难以开导自己。如果和别人倾诉,“他们会说我想多了,那件事和我没关系”,她感觉自己陷入了死胡同。
陈小丹还心怀愧疚。朋友曾在谈话中透露出厌世的态度,但她“乐呵呵地还看不出来,以为他单纯就是喜欢聊这方面的话题。”看到遗书时,她不理解朋友的选择。他条件不差,有书读,有朋友,为什么离开是“喜悦”的?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朋友身上?这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学生辅导中心的咨询师Silver Chan在进行心理支援时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多数时候,情况比较复杂。她避免把自杀归因于某一个因素,把重点放在帮助学生处理哀伤的情绪上,让他们在安全和开放的环境中表达。在小组辅导中,许多学生会分享和离世同学的回忆,给她看旅行和生活中的照片。Silver说,多数学生会在2-3个月内处理好自己的状态,少数人受到的影响可能会长达一年左右。
那段时间,父母担心陈小丹的状况,往学校跑了好几趟。她周围的同学也发现了反常,和辅导员反映后,学院为她安排了一位心理咨询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所重庆的一本学校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每学期开学,辅导员都会把预约电话发到班级群里。
陈小丹每周去一次。开始前,咨询师会让她坐在按摩椅上放松一会儿。起初,她不愿讲那件事,一提起就崩溃大哭。咨询师让她把道具摆放在沙盘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她铺得密密麻麻,咨询师问:“你是不是有很多话想说?”
咨询师推荐了一些心理学书籍,帮助她理解自己的感受,建议她把每天的心情记录下来。陈小丹的情绪时好时坏。最抑郁的时候,结束咨询依旧很低落,“我以为心理咨询就像是魔法一样,结束了心情就会变好。”咨询师告诉她,这并不是万能的方法,重要的是把感受通过合适的方法发泄出来。她想起离世的朋友喜欢跑步,于是会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出门跑几圈。
两个月后,她第一次和咨询师讲述了那晚的经过,对方很惊讶,这代表她已经能面对那件事了,“心理恢复能力挺强的”,陈小丹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最后一次,陈小丹摆放了一个海边的房子,画面悠闲宁静,咨询师看出她的状态好转,“恢复七八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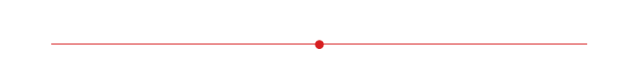
“你有我们的支持”
今年九月,林雪莉进入香港大学建筑学院读研。9月30日0点50分,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校长的邮件,红色的叹号后跟着“You have our support(你有我们的支持)”。平时学习忙,社团招新、心理咨询之类的邮件都被她归为“比较水的那种”,只有老师和校长发的才会特意打开。
“亲爱的同学们、同事们,当我们今天得知一位学生的悲剧时,我很难过地写信给你。我写这封信是为了表达我们最深切的哀悼和对港大社区的支持。港大已与学生家属联络,并会向他们提供适当协助,我们会竭尽所能支持所有受这场悲剧影响的大学成员。
如果你对这件事感到担心或痛苦,不要把它藏在心里。请通过电邮或致电与CEDARS(学生发展及资源中心)联络。如果你想与人聊天或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全天候运营的网站。
亲爱的同学们,生活可能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挑战,但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请记住,你们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寻求帮助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你并不孤单。我们永远在你身边。”
看到最后两句话,林雪莉很感动,把邮件截图分享给本科时的同学。
她从前就读的211学校发生过多次自杀事件。一次学生跳河后,有警察来到学校,那条河被围了起来,老师让大家不要传播这件事,注意自己的身心健康。但学校越是“压”,林雪莉的好奇心反而被激发起来,“越想八卦”。“关注身心健康”也更像是在喊口号,她只感到压抑。
陈小丹也被老师提醒过,不要公开传播那件事。这是许多内地高校常常采取的做法。河北省教育厅印发的《河北省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手册》中提到,为了减少不知情人的猜测议论甚至恐慌,辅导员应将学校官方统一发布的公告简明扼要地通知给自己所负责的班级,教育引导学生不随意到网络上参与事件的讨论,未经允许不接受媒体采访。
10月12日晚,香港中文大学发生了一起跳楼事件。很快,港中大内地本科生联合会会长张艺看到了传闻。晚上十点,她向管理学生事务的副校长发邮件询问。第二天,副校长在回信中确认了死亡事件,但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也出于更多公众信息方面的考虑。在这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学校制度的目的。”第二天,学校在官网发布了确认学生离世和表达哀悼的公告,和死者同书院的学生都收到了提供支援的邮件和短信。
这些邮件通常使用“悲剧”“离世”来称呼自杀事件,其中不会透露死者的个人信息。香港科技大学学务长周敬流介绍,在尊重死者家属意愿的前提下,当自杀事件发生在校内公共区域,可能有较多目击者时,校长通常会发邮件给全校师生及职员,表达哀悼和安慰,当自杀事件发生在私人场所,学校一般会面向和自杀学生同院系的师生发布邮件,提示大家可寻求心理支援的途径。
周敬流说,过去十多年,学校都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哀悼与安慰。公开的表达有助于安抚大家的情绪,并提醒受影响的人群寻求帮助,尤其是认识死者的职员和学生。对他们来说,这种影响可能是创伤性的,“就像面临家庭成员的死亡一样,而不仅仅是新闻报道”。
自杀事件发生后,通常会有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表达哀悼,因此发邮件也意味着向社会面传播这个消息。香港媒体的反应通常很快,有时跑在校方公告之前,甚至比老师听说的都快,从现实来说,“你想保密,保不了”。周敬流认为,自杀事件也不应该被压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地把它拿出来,公开地去讨论什么是比较积极和正面的做法。”
香港教育局发布的《学校危机处理手册》提到,学校可透过安排追思活动让学生表达对死者的怀念及抒发哀伤情绪。但应避免任何会美化自杀行为的活动,例如:在校内举行大型集会;为自杀事件或自杀死者设立永久的纪念物,例如纪念碑、艺术品或在校刊悼念死者等。
校内发生自杀事件往往被大众视为负面消息,周敬流认为,虽然事件发生的地点在校园,但自杀的原因来自很多方面,学习压力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不该将学生自杀与学业因素直接联系起来。“自杀事件发生后,学校并不会受到来自政府或教育部门的压力。”周敬流说,如果高校的自杀个案比较频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或教育局会向校方确认是否有采取措施改善情况,是否需要提供支持。
香港科技大学指导学生面对悲伤情绪的宣传单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杀和心理健康问题不是禁忌和敏感的话题,学生们往往能和校领导及老师进行平等的沟通。成曼丽在香港大学读大二,一年多来,校内已经发生了四起学生自杀事件。她曾上过一门性别研究课,在一次关于性少数群体的课堂讨论中,老师主动提起了那年8月初的一起自杀事件。老师说,那名女生的死因与自己的性别认同和家人的反对有关,并告诉大家,如果遇到了类似情况可以向校内相关组织寻求帮助。
陈泽宁是香港中文大学内地本科生联合会前会长,2020年疫情期间,他关注到随着学校开始上网课,一些内地生回家后可能被封控,出现家庭矛盾,负面情绪可能会加重。联合会和副校长进行了一次线上会议,他们提出了10多条举措,最终学校和深圳校区达成了合作,因疫情无法返回香港的内地生可以去旁听课程。学校还拨给了联合会一笔资金,用于联络校外的心理辅导机构,为同学提供服务。
今年10月,香港高校连续发生数宗大学生和年轻人不幸离世的事件。香港八所大学的学生事务代表于2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大学生、社会上的年轻人和家长分别给出建议,呼吁在各方同心协力下,共同建立促进心理健康、逆境自强和结伴同行的文化。
周敬流在科大任教20余年,他感到如今学生的学业和人际关系压力比从前大了很多。五年间,学生辅导中心的咨询师从8个增加到现在的13个,每天的时间表都被排满。
张艺也感受到学校心理资源的紧缺,从预约到接受咨询,往往要等上一段时间。在10月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有人在身上覆满印有“预约全满”“家庭关系”等标语,以行为艺术的方式呼吁校方关注学生的精神健康。
四年过去,陈小丹已经从学校毕业。她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正在准备考研。她仍会梦见那位自杀的朋友,只是他们之间一些普通的日常。但有时,那晚的情景还是会不受控制的地闯入脑海里,她只能使劲闭上眼,强迫自己睡去,“也许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也许我会经历更多事情把它掩盖掉。”
每到朋友的祭日,她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他纪念。有时写诗,有时分享歌词,有时记录自己的感受,发在一个没有人关注的角落。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陈小丹、成曼丽、林雪莉、张艺为化名)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 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
最新文章

广东韶关,“猩猩”爬墙?,黑冠,亚科,猕猴,猴子,藏酋猴,猩猩属,韶关市,广东省,广东韶关,受威物种,濒危物种,野生动物
(0)人喜欢2023-12-10
实探北京儿科就诊高峰:“采个血要排到500多号”,多家医院优化就诊复诊流程,急诊,就诊,儿研所,北京市,儿童医院,复诊流程,长峰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湘雅二院一医生被曝医疗作风有问题
(0)人喜欢2023-12-10
2023张韶涵「寓言」世界巡回演唱会-厦门站将于7月15日(周六)19:30在厦门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演唱会大约多长时间结束?厦门本地宝为你解答。
(0)人喜欢2023-12-10
省委书记直奔小区 接自来水喝查水质
(0)人喜欢2023-12-10

香菇特有的香味,做出的汤特别的鲜美,再加上豆腐鸡蛋的滑嫩柔软。香菇木耳鸡蛋豆腐汤不仅味道好,而且营养十足。香菇木耳鸡蛋豆腐汤的做
(0)人喜欢2023-12-10
在游戏《原神》中,原神岩之印获得方式是地图探索和岩神像升级。岩之印是会刷新的,因此玩家可以在同一个地点多次获得岩之印。岩之印可
(0)人喜欢2023-12-10
现在我国已经在全面开放二胎了,因此全国都已经取消准生证的办理了,生育两个以内的孩子的夫妻可以自行安排生育,之后进行登记即可,不需要
(0)人喜欢2023-12-10
在期货市场中,据专业数据统计,有70%的投资者都是亏钱的,有20%的投资者不亏不赚,只有10%的投资者是赚钱的,以下简单总结了几个原因:1、专业
(0)人喜欢2023-12-10












